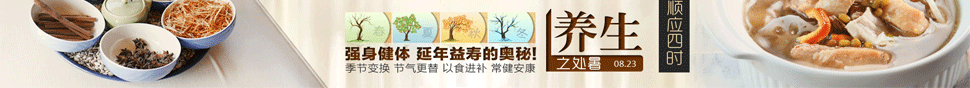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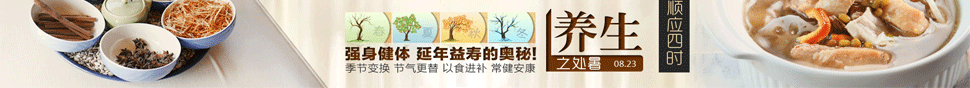
石板街(《民谣》中的重要背景)
文/程德培
“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这句激励作者写下四卷正文的长篇开头,我们早在十几年前就听说了,笔者也依然记得作者在讲解这一开头时的眉飞色舞。那个年头,不是小说家的讲解自己正在准备写小说的人多了去了。不料今日王尧梦想成真。在二十年的漫长书写过程中,故事的跌宕起伏早已化为历史的烟云,留下的只是琐碎的细节,东鳞西爪的残言,无法复原的片断,不断流失又不断修复的感受,不断遗失又不断被想象修正的记忆。尽管如此,开篇依然挺拔,以至在收尾时重复出现。码头如此重要,那屁股底下的一张薄纸也不是可有可无。
成长中的“我”虽然年少无知,但借助码头上的左顾右盼,凭着家族的渊源,向左延伸至外公的革命史,向右延长至小镇上奶奶的家族史。而两次大火又分别连接着两家人的命运:大火后的天宁寺留下的遗址上有王二大队长和剃头匠的革命烈士墓和谁是叛徒的秘密;而镇上石板街曾经着过的大火则改变了爷爷奶奶的家庭成分,他们从此也从镇上迁到了村庄。
“让父亲一辈子记住的是怀仁跟他说的那句话:‘你之前是少爷,现在不是了。’”外公和奶奶的两支来源,如同《民谣》的两翼,如何延伸和飞翔全凭着两翼的舒展了。两次大火无疑是“我”的家族史中的事件,意料之外的突然事件给家族带来了不测,使其充满不可预测性和偶然性:外公因“事件”革命史受到质疑,奶奶家则因命运改变而躲过一劫。“我”的家族则在两次大火后,在年经受了共同的恐惧。
年仅14岁的王厚平,面临着历史疑云、世俗困境的重重阴影,除了疑惑还是疑惑。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设疑、解密和不着边际的交锋后,我们这位年轻的队史撰写者,终于在码头上等来了从公社归来的外公,“差不多半年,外公的历史问题快要有结论了。我从来没有想到,外公成了村庄一条即将理清且要打结的线索。‘厚平,你外公的问题有了结论,我们这个大队的革命史就好写了。’昨天下午队史编写组的会议结束后,勇子悄悄跟我说。”
另外,江南大队等来的石油钻井大队除了给村庄带来新的希望,工人们也给乡村的尘世生活带来了新的风尚。那些工人身上的中华牙膏、自行车、帆布包、皮鞋以及姑娘们的裙子和雪花膏,也和奶奶封存已久的神秘箱子里的旧物件,有了某种隐秘的贯通。两个时代的“洋货”虽不相同,但“两个错落的时空,在我心中重合了”。“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明白了奶奶是这个小镇的象征,也是旧时代小镇的延续。
其实,小镇和村庄有太大的反差,但奶奶没有表现出痛苦。她在记忆中,在生活中不断延续的那个旧时代,给她带来了平衡。在我开始学会思考的时候,痛苦便随之而来。我这个时候会觉得奶奶比我幸福和充实。我找不到一个让我内心平衡的世界和记忆,唯一能够抚慰我的方式,是我自己不时想象未来。”至于王厚平内心排斥的奶奶那一辈人的生活什么时候会卷土重来,那已是飞越《民谣》之外的事情了。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小说中看到那充斥着隐喻的场景:患有“神经衰弱”的“我”,整日捧着一只药罐,靠吃药长大的王厚平。“几个月了,我一边吃药,一边想着去年春天的下午,想起那把洋伞,想起白胡子老人说的我不熟悉的地名,想起在静静的空巷中与他亲热地问答。”“我没有听见脚步声,但突然有个老人摸了我的头。”“这老人好像说我外公去过那个地方,他怎么会知道我外公?我对村庄之外的许多向往,都贯穿在我对那个地名的猜测之中。我甚至觉得与外公相关的故事都与这个地名有关。我记住了这个下午所有的细节,但我就是忘记了那个地名。”
这次源于虚幻的相遇,借助梦幻般的记忆,在王厚平那稚嫩的笔下化为一个高个子老人和一个矮个子少年的图画,伴随着“我”一同成长,夹在晓东留给我的《红旗谱》中。几年后,在小说将要结束的时候,“这个少年长高了,如果重画这个场景,他和老人的比例要发生一些变化。”即便如此,白胡子老人所说的地名,至今仍无法说出。
莫言为《民谣》题名
写作了那么多年的《民谣》,最后抵制的却是故事,或者说是那些制约或抵制记忆的故事。记忆从不遵守情节规约,它是散漫无序的,它无意去重新激活那无数固定不变、死气沉沉、支离破碎的旧日痕迹。记忆总是运用想象力去重组或构建,这种重建是基于我们自身的态度和看法;我们对过往经历的态度,以及我们对于一小部分鲜明细节的态度。记忆总是伴随着遗忘,总是对遗留碎片的摹仿,对遗忘缺口的补充想象。正如王尧自己强调的:“许多东西就是这样,你以为它死,它却活着,你以为它活着,它却死了,还有许多半死不活的状态。”
《民谣》反故事。很多时候很多地方可以写成像模像样的故事,作者宁舍不取,忽略不见。王尧反故事不反历史,相反他尊重后者,力图复原真实的历史场景。记忆不同于虚构,但在作者看来,它们又共同服务于历史。他甚至大胆直呼:“个人是细节,历史才是故事。”他同时也直言告白:“故乡是我写作的种子,还是这颗种子最初的土壤。”
恰如J.希利斯·米勒所言:“‘小说家的叙事是历史’这一设定,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只是简单地给他的作品一个基础。它同时‘在他的企图中嵌入了逻辑作为支柱’。倘若没有‘具有一种历史的根基’这一设定,一部小说似乎就会土崩瓦解,变成互不关联的碎片瓦砾,或者用亨利·詹姆斯的名言,就会变成一头‘庞大散乱的怪物’,成为无脊椎动物,优柔寡断之人或是美杜莎。唯有设定它就是历史,一部小说才会有开始、连续或结尾,也才能形成一个首尾一致的整体,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或是特有的个性,就像一个有脊椎的动物一般。”
《民谣》作者王尧
《民谣》的断断续续写作,作者工作繁忙是个原因,但我认为重要的还是写作的难度。小说涉及的具体时间段才那么几年,但其容量极大,头绪繁乱,源头悠远,路径不一,故乡连着他乡,村庄接着小镇,传统时断时续,革命与现代性犬牙交错,成长过程似懂非懂,语境似明非明。
恰如在睡眠的边缘,那些我们看似依旧处于睡梦状态的东西转变成了现实,而那些认定为现实的东西回过头却是一场梦。文化变迁总是既梦又非梦,既包括重点的明显转移,又包括相当的持久性和连续性。以一个成长中的小男孩视角观察和感受,让他背负着记忆的重负,充当虚构的机器,通过将线性的叙述移动到隐喻的齿轮,在作品中安排文学准则的冲突,分散在秩序中并整理了混乱。
在含沙射影中点出真相,用寓言显现观点,机缘巧合装点隐含的晦义,奇闻轶事变成了修饰语境的符号,或者换用政治事件、革命运动、一度流行的读物、歌曲、民谣来暗示时代变迁的暗流涌动……要做到这一切,难度是可以想象的。
其难还在于,这是王尧首次写小说,一写就写长篇,还是这么复杂的长篇,自我的操练和借鉴几近空白,可谓难上加难。当然,小说创造史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有码头的故乡总是和流水分不开,它可是离家和回家的地方。王尧笔下的故乡总是流动着:一头流向祖父辈的过去,一头则流向“我”的少年记忆。《民谣》的时针不会是卡夫卡式的静止不动,人们只能生活在充满着烦躁不安的现时的片刻里,因为他们竭尽身心之力去寻找那不是他们所能找到的真理;它也不会是乔伊斯式的时针,以联想来推动,不停地改变方向。尤利西斯的题材不是有时空限制的一次事件,而是一次灵魂的阅历,其象征性包含着“所有的死者与生者”。
王尧的时针更倾向着普鲁斯特式的,时针是倒行的,从记忆出发,还给我们以遗忘了的经历。不同的是,对普鲁斯特而言,充满希望的大地就是那过去的乐园;对王尧而言,那逝去的时光,不乏灾难性的创伤,恐惧不安和少年无法承受的迷惑不解。
想想小说开首写的那场无法忘却的大暴雨,“在后来很长时间,年5月的大水,让我觉得自己的脖子上挂着几根麦穗。记忆就像被大水浸泡过的麦粒,先是发芽,随即发霉。我脖子上的几根麦穗,也在记忆中随风而动,随雨而垂”。少年的嗅觉如此灵敏,以致记忆的字里行间充斥着霉味、药味、油墨味以及渔网上传来的腥味。
“我”和外公们是命运共同体,就好比“少年的我,除了喜欢看自己的成绩单外,就爱读布告。而在外公的名字也出现于墙上的大字报上后,我尽可能不从这边路过。”然而,“我”和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又是不一样的,“我无法理解父母亲把神经衰弱的病因归为去年春天我与白胡子老头相遇。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他们毫无兴趣。我无法忍受,我如此真实的经历会被大人嘲笑为做梦。”“那时我会觉得白天看到的是虚幻的,晚上所见是真实的。我常常在夜晚充满了想象,我在想象中推翻或肯定我的所见所闻。”
白天夜晚的颠倒有时恰恰歪打正着,揭示某个秘密或某种真相。这既是一种意外收获,也是对少年行径的真实写照。王厚平身上往往具有男孩们所特有的情感,渴望加入专门的圈子,渴望遇见神秘之人和神奇之事,加入一种使用接头暗号的秘密团伙,还有对那些掌握某种技能、多少有些神奇又能驾驭他人的成年人仰慕不已。他对自我与世界的区分是缓慢发展的过程,他们甚至对早早到来的性启蒙既感到害怕又有着本能的渴望。一个少年典型的英雄梦和情感启蒙,我们只要简单地回顾一下王厚平的阅读史就略知一二。
着迷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战争与爱情,冬尼娅的幽灵甚至跑到方小朵身上去了;能够背诵《野火春风斗古城》中金环的遗书;沉湎于《红岩》的江姐、甫志高和双枪老太婆;钟情于《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和白茹,难忘《红楼梦》中的爱情悲剧等等。最离奇最真实的,要算一本《赤脚医生手册》给予“我”和余明的性启蒙。试问,只要是同时代的过来人,谁又没有过这样的阅读取向。
《民谣》写的是乡村少年,我则成长于城市的亭子间,而在那个时代我们的阅读方式和截面倒是城乡“一体化”的。在那些不多的书中,不管有多厚,我们都能熟练地翻到吸引我们的段落,索取我们想象中的内容,从来不管这是正阅读还是反阅读。
年12月6日于上海
(此文为节选)
(本文为王尧所著《民谣》的书评书选内容,由译林出版社授权发布)
华文好书选读
《民谣》
王尧
译林出版社
年4月
“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
时间拨回至一九七二年五月。依水而生的江南大队,漫长的雨水终于停歇,麦子发酵味道笼盖村庄,暗潮涌动于日常。码头边,十四岁的少年等待着了解历史问题的外公,江南大队的人们等待着石油钻井队的大船,然而生活终以脱离人们预计和掌控的方式运行。少年在码头边左顾右盼,在庄舍与镇上间游走返还,在交织缠绕的队史、家族史间出入流连。他于奔跑中成长,于成长中回望,回望里,记忆发酵,生长。历史老树的黄叶,一片片落入《民谣》的故事和人物,飘扬,旋转,飞翔。
作者王尧为其首部长篇《民谣》准备了二十余年,藉此完成了他重建个体与历史之间联系的夙愿。他以故事中人与故事看客的双重身份,杂糅评点、抒情批判,岁月流逝中的碎片和碎片不断碰撞,显露出新的缝隙,而小说由此拼凑出一条真正能够进入历史的现实路径。这里有故事,但波澜不惊;它从历史走来,也脱胎于每个日常;散曲民谣中包裹着唱不尽的人事变迁与世情冷暖。《民谣》铺写一个少年的成长精神史,一个村庄的变迁发展史,一个民族的自我更新史。它以个体细微纤弱之小记忆,呈现时代的宏阔酷烈。
华文好书
ID:ihaoshu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