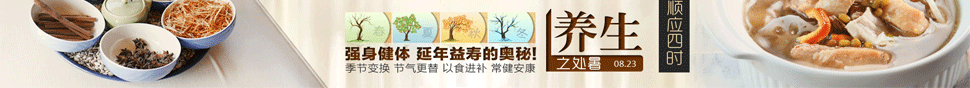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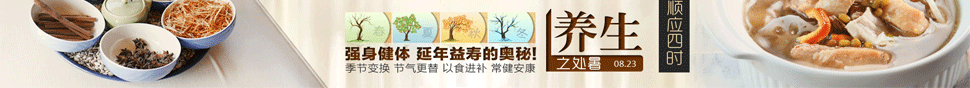
唐音宋调,是指唐诗、宋诗两种不同的类型,却不能单以时代划分。这是因为“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而宋以后的历代诗人,“所作亦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钱先生所言,涤除了古代诗论过分以时代相区隔、颟顸对立唐宋诗歌的局限,为我们客观评价宋诗与宋调提供了新的视角。
北宋边塞诗中的唐音延续
就唐代边塞诗而言,它多呈现出奋发有为、慷慨激昂、雄豪尚气等精神气韵,并在投笔从戎、视死如归、精忠报国、以战求和等主题中发扬光大。这种时代气韵的凸显,常常借助描绘奇绝壮丽的风光、塑造生动鲜活的形象、经营意象密集的画面,从而营造出深邃感人的意境,以情动人。
北宋边塞诗中的唐音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突出,一是乐府边塞诗,二是宋初边塞诗。究其原因,一方面与乐府诗自身的体式特征有关,另一方面,北宋初期宋调未立,诗歌创作仍在唐代艺术经验中寻求路径,因此从这两个角度出发能集中揭示其唐音面貌。
一、乐府边塞诗中的唐音
北宋边塞诗沿用前代乐府诗题,借《塞上》体现征战,用《关山月》《寄衣曲》传递相思,在《从军行》中砥砺建功,均有唐音韵致。
第一,《塞上》《塞上曲》《塞下曲》诸题中的征战表现。《塞上》尤为宋人推崇,北宋前期的柳开、王操、谭用之,以及中期的胡宿、余靖、司马光、陶弼都作《塞上》边塞诗,其中司马光一人独作五首。
以柳开、司马光《塞上》为例析之:胡儿骑兵在天静无风的静谧中行进,画面的静谧被突然划破长空的骹鸣打破,全诗收束于胡儿的抬望,至于其心理变化则留给读者发挥想象。全诗经营画面,动静对比,调动读者多重感官,含蓄留有余味,深得唐诗真髓。
与柳开诗大量留白、经营余韵不同,司马光诗意更加深刻,直斥赏罚不均与将士牺牲。司马光恰是北宋防守战略的倡议者,其诗不仅从诗艺上继承唐诗,亦在边见上引为知己,故能感发人心。
第二,《关山月》《寄衣曲》中的思乡怀人。《关山月》为思乡念亲提供了有益借鉴。北宋一朝,创作《关山月》的有宋构、文彦博、张舜民,均继承前代经验,表达清晰的情感指向。
其中,宋构《关山月》在关山、陇上行人、明月之间营造乡思,“一声羌管裂青云”以响托静,从听觉上丰富了艺术体验,多角度地渲染了人物的孤孑处境。诗人为思妇代言,思妇的心态调整实际是宋人的心绪写照,其由相思“生怨”到相思“理解”的心态转变,是宋人取径唐人的结果。
第三,《从军行》中的军功砥砺。《从军行》本为“述军旅苦辛之词”,至唐,已有“从军苦”与“从军乐”两种范式。文彦博《从军行》虽描写严寒,却未顺着苦寒蔓延,而是传递出立功封侯的积极面貌。此外,苦寒抒写亦被植入多种乐府诗题,由边地苦寒进入抒发边思、激励边功、同情战士等情感内蕴,是唐代边塞诗留给宋人的宝贵财富。
二、北宋前期边塞诗中的唐音
北宋前期诗人,边塞诗有唐人风致者,如谭用之、张佖、张继常、郑守文、王操、张咏、刘、赵湘、寇准、穆修、唐异。在北宋前期的诗学视野中解读张咏、寇准边塞诗,可以清楚地看到其追摩唐人的良苦用心,亦可见其由此带来的情感差异。二人诗风虽有不同,却皆得唐诗言情风致。
方回在《桐江续集》卷32《送罗寿可诗序》中首次提出“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之说,并将张咏置于“昆体”。然观张咏边塞诗,并无昆体辞采婉丽、善用典故的特点。
此诗非但未有浮艳华丽、刻意经营的昆体特征,反有“语言质朴、章法顺畅”的白体风貌。诗意由不惧边务、御边闲适转入家国寄责,皆以情驭景,切近戎事。“高栏是夕攀”亦营造出登临之感,这种空间布置,为画面的接续、情感的流动精心酝酿。
再看寇准诗,则无张咏诗之气定神闲、意境淡远,而是沾染了晚唐诗特有的清苦:诗人借助“穷边”“秋林”“天寒”“碛迥”等意象营造出孤峭凄清的意境,凸显出戍楼独听的孤孑。同为塞上感怀,张咏《登麟州城楼》由边苦宕开,终于报国之雄健,寇准《塞上秋怀》则由边苦切入,终于戍边之凄凉。
还需注意的是,北宋前期出现了一些僧侣边塞诗,多展现了宋辽对峙的时代画面。正如鲁迅所言:“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可见,在北宋前期的边防形势下,宋辽战和亦影响释门创作。当然,即便在宋调确立之后,唐音亦未绝迹,只是被宋调的显性特征遮蔽。
北宋边塞诗中的宋调新声
北宋边塞诗的“宋调新声”归根结底是指从主情尚虚到主理务实,从经营意境变为烘托事境、叙议相彰,呈现出“学人之诗”与“才人之诗”的面貌。作为开创宋调的代表诗人,苏舜钦的边塞诗最能体现新变之征,所作《庆州败》《己卯冬大寒有感》《送安素处士高文悦》《瓦亭联句》《串夷》,皆叙议横生,情理兼具。
宝元二年,苏舜钦作《己卯冬大寒有感》:西夏频频犯边,先后于春秋两季入侵鄜延路、镇戎军。烈士的壮节,治军的训诫,前线的战况,边民的困弊,随着诗人清晰的理路与犀利的论说喷涌而出。全诗论边如同奏疏,将边事废弛、措置无方、边民困窘随事列出。
随着边情回顾与战事描写,壮士誓死卫国、懦夫贪生蒙羞的强烈对比将诗歌情绪推向沉郁,最终收束于“早令黠虏亡,无为生民孽”的诅咒与扼腕。
观北宋前期的诗学探索,宋初三体先后取径白居易、贾岛与姚合、李商隐,但是,追摩上述前贤并未实现自立宋调、创变诗歌的终极目标。庆历前后,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士大夫,其知识结构趋于综合,复合型人才的主体人格亦渐趋确立。
随着治政的纯熟,他们选择诗学偶像的标准与能力均远迈三体,以杜甫、韩愈为师,兼收并蓄,总萃诸家,是庆历诸公的自觉选择。
而师法杜、韩,本身就有偏离“含蓄有味”的“隐患”。杜甫的直抒胸臆,韩愈的以文为诗,本身就与含蓄相违,加之宋人晕染发挥,难免带来诗意的直露。结合欧阳修的人才观念,可知其对议论、博学的弘扬,如称赏苏洵“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赏爱苏轼亦因为“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论议蜂出”。
欧阳修之后,苏轼为盟主,推进“宋调”亦不遗余力。至宋调成熟的元祐年间,北宋诸家不仅在态度上愈发坚定,在文艺上亦驾轻就熟。
综上所述,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庆历诗人与以苏轼为盟主的元祐诗人在推进宋调的同时,亦不自觉地将叙事、好议、说理等手法注入边塞诗创作,令学人之诗与才人之诗的味道更浓。
北宋诗家急于求变,破体为新,增扩容量,赋予诗歌太多补裨时政的功能,故为后世诗论家诟病。观后世的诗学批评,从唐诗专好到唐宋诗各有特色,拂拭偏见十分艰难,归根结底是对言理、议论的批判。从张戒揭开扬唐抑宋的序幕,至严羽进一步深化唐诗风格学,降至明代许学夷,审美功能的评判标准一旦确立,很难对宋诗给予客观评价。